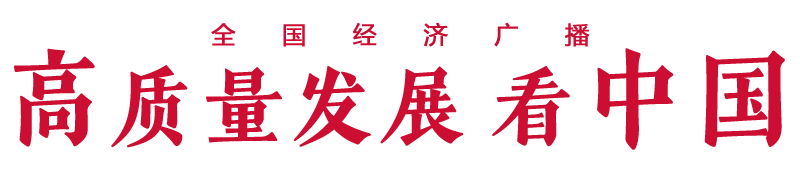文/张毅龙

晨光初透时,小圃里的花正带着露水开放。那晶莹的露珠,像是夜色凝成的泪,又似晨光初酿的蜜。我从不刻意照料它们,只是静静地看;看花瓣如何一瓣瓣挣脱苞衣的束缚,完成一场沉默的爆炸。这便很好。案上的深杯已满,酒香沉潜,不似花香那般招摇,只在属于自己的方圆里,营造一片微醺的天地。
转身望向窗外,旧篱边的菊正纤纤而立。枝叶半卷着,似畏清寒,又似含羞。叶上瓣上,昨夜的白霜还未化尽,褪去了金绮衣裳,只留下湿漉漉的憔悴。都说“玉容憔悴”,可它在瑟瑟风里立着,偏生出无限情味,引着人不得不看,不得不思。
这便是我的日子了。“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这“自”字,是何等圆满又何等孤绝。歌不必有听众,舞不必有看客,悲喜如云卷云舒,来便来,去便去,不留一丝黏着的痕迹。忽然想起白云泉——“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云的无心是不牵不挂的飘荡,水的自闲是不竞不争的流淌。它们何曾想过要奔冲下山,去人世间再添无谓的波浪?
心思飘忽间,恍恍惚惚回到旧岁光景。也是这样的秋深,那时的菊闹嚷嚷开成云锦。嬉笑间,带着凉意的花瓣不经意沾满衣袖。疏影里,秋虫幽幽吟唱,为已逝的繁华唱着低回的挽歌。最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黄昏与友人同醉东篱后,他将满眼秋色收拢到素纸上。墨痕在纸上慢慢润开、凝定,仿佛不是画,而是将菊的香魂一并融在笔底。这哪里是画?分明是一整个可以珍藏的秋天。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史册上浓墨重彩的将相王侯,他们的功业如今安在?不过是一场做得长些的春梦,梦里金戈铁马,梦外荒冢一堆。我们又何须将自己的一生,去与那些遥远的魂魄计较、安排?生命的真谛,或许不在身外的求索,而在于内心的“领取”。
领取而今现在。这“领取”二字,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不是在时间里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地、深情地拥抱眼前这一刻。是月夜下,那部清商伴着的“老身”;是饱食安眠后,闲谈冷笑里的交亲。终于明白,在将相王侯的煊赫之外,别有一种优游快活的人生。
今朝独自对着这菊,心里生出更深的怜惜。我们这般相逢,竟像各自怀着说不出的幽恨;它那凄凄然的细香一阵阵传来,仿佛不是闻到的,而是听到的,是一阕无声的哀婉曲子。眼虽凝望着隐绰菊影,心却早已不在这里;像倦飞的鸟,倏地越过斜阳,没入远山之外的云岫。只盼在梦里,托风儿捎去前语,再看看那“一枝斜照水”的清姿。
心既飞得远,人便也跟着去。去的是空山,欲晓未晓的时分。疏林攒着薄雾,像一袭拂不开的轻愁。生苔小径上,寂静得只听见步履声,一下,又一下,叩问着无言的清晨。独个儿在溪边对着冷寂景色出神许久,偏有翠色小鸟跳踉鸣叫,像旧相识,又像特意来旧游之地寻觅往日痕迹。
最教人萦怀的,倒不是盛大筵席,而是那回在友人山居,黄昏时他随口说“夜雨剪春韭”,便真到园里割新韭佐酒。我们喝着浑浑的、暖烘烘的村醪,直喝到醺然欲醉。窗外是沉沉的夜,屋里亮着温然的灯,共话着,将半窗夜色话成青碧融融的一片。可时光如无情西风,浩浩卷地而来,萧萧然掠过千山,将熟悉的云容山色顿然改换。
醉中题句总是酣畅;醒来对着淋漓残墨与苍崖上将尽的斜阳,心里只剩茫茫怅惘。于是转身走入幽深竹林。对着万竿凝翠,听着风过处清冷的微响,不知不觉,天边那轮冰魄似的月已缓缓升起。清辉泻在竹叶上,也泻在衣上,仿佛要将魂魄一并凝住。那时痴痴地想:总还能再见的罢?总会有那么一天,重新把翠樽捧在手里,倚着寒柯,一同看苍翠山峦在眼前历历分明。
这念想送我走上晓雾濛濛的山路。石阶是湿的,沾着露,留着前人或昨日的履痕。一步一步向上走,走到云开雾散、豁然开朗的顶处。那时万座峰峦如少女青黛,绵绵邈邈与宽展的天连接一处。也曾去寒谷,看冰封小径上雪满蹊跷,却有一树孤梅用它疏朗的影子,静静破开压境的霜枝。暗香浮动,随风远引,才引得我这般的骚人,不辞踏雪,来迟一步。
此身此心,当如白云任卷舒。天涯海岸皆是故乡;太虚廓落尽为吾庐。功名如拱璧,华屋不过轩车,都抵不上“一味闲闲”的乐趣。活计不妨冷淡,世途任他消疏,我只问归来之时,此心何如?
但见心月辉辉,光明澄澈,清辉洒落之处,虽是简陋蓬壶之居,也仿佛成了晶莹琉璃世界。至此,方是“陶然无喜亦无忧”的究竟境界。喜与忧依旧是情绪的波浪,而真正的自由,是波浪之下深湛宁静的海床。
许许多多的往事,到如今真如烟一般,逐水流去。浮生聚散何尝由得人留?倒不如看淡尘嚣琐事,学古人醉卧清风,头枕冷石,悠然地自得其乐。想古人躬耕陇亩,以茅舍疏篱与竹轩为伴,便避了尘喧;醉里挥毫,胸中自有丘壑,便不羡世间功名与神仙。这境界虽不能至,却总是心向往之。
那抚琴溪畔,石上清商一曲随流泉漂远,山风传韵,竟引得孤鸿落于碧天——这等风雅,而今安在?便学他一个“醉卧松风枕石眠”,拿流云作被,明月为毡,也是好的。待到醒来,真个可以不问人间是非闲事,只闲闲地,看青翠山峰如何静静地,挂住破晓时的一缕烟霞。
立在这冬日的清晨里,看初升太阳将无垠雪地染成细碎金箔。路边树梢裹着蓬松棉絮,阳光一掠,便有点点雪末闪着细碎的光,无声坠落。早起的人踩在积雪上发出“嘎吱”声响,在这空旷静谧里,不觉得扰攘,反成了冬日晨曲里最教人心安的音符。
没有白日的喧嚣,也没有夜晚的死寂,这一刻的世界纯净得像未经雕琢的白玉。而那关于旧篱、清霜、残墨、孤梅与空山的种种思绪,也在这无边的纯白与宁静里慢慢沉淀,化作心底一声极轻、极满足的叹息。
夜又深了,依旧是可怜月好风凉。我且将这满杯的酒,敬给天上的月,水边的楼,敬给这无拘无束、领取而今现在的,自由的人生。

(张毅龙,湘人,曾务农、做工、执教,诗文散见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