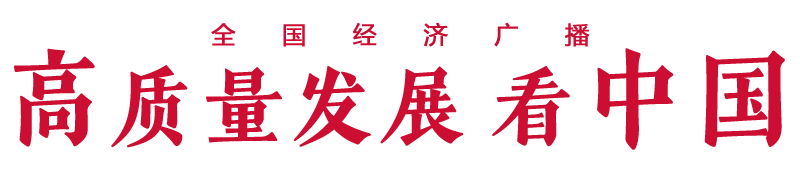作者:张毅龙
这西楼,怕是专为无眠之人而设的。夜气自四面八方围拢来,沉甸甸地压在栏杆上,冰着我倚靠的手腕。栏外的虚空里,一轮凉月,正不声不响地,一步步踱进楼来。那光也是凉的,像一道清浅的溪流,漫过我的袍角,我的襟袖。流光仿佛在此刻凝滞,化作薄霜,覆满雕栏。我便是那“倚栏无语久”的痴人,天地间只剩下这一片静,静得能听见流光从指缝间滑走的声响。
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越过这清冷的月,投向那更深、更远的黑暗里去。那里该是“露浓湘渚阔,风急楚云秋”的所在罢?千里之外,你是泊在那样开阔而凄寒的江渚旁么?我这厢的孤灯,将我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壁上,那影子也是愁的,瘦怯怯的,仿佛一阵风来就能吹散。“千里人何处,孤灯影自愁”,这灯与影,竟成了我唯一的伴侣了。
总想着能托付些什么。古人说雁足传书,鱼腹藏笺,可我举头望去,夜色沉沉,连半片鳞鸿的影子也无。“欲托鳞鸿去,音书不可求”,这徒劳的念想,比彻底的绝望更磨人。记得你离去时,正是“篱菊开时君始去”的光景,如今眼见得“菊残人尚未归”,年光已逝,人迹杳然。那挟着寒意的西风,吹动我的衣袂,恍恍惚惚,竟像是你征衣上拂不去的风尘,带着别时的泪痕。
这般情境,不由得人不生出些颓唐的感慨。古人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笑“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他们说得何等洒脱,“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又说要“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要“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更有那旷达的,于“穿林打叶”声中“吟啸徐行”,觉“竹杖芒鞋轻胜马”,最终悟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理。这些话语,字字句句都像温润的玉石,熨帖着千古以来所有焦渴的心肠。
我也曾神往于那样的境界。“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或是于山中,“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再或如那碧山中的隐者,看“桃花流水窅然去”,安享那“别有天地非人间”的闲适。总想着,人生于世,便该如那“野鸟投林”、“渔舟冲浦”一般,“万物各有适,人生且随缘”才好。
然而,道理是这般分明,心却总是拗着。那“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的苍茫,“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的冷寂,我都懂得。也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四季佳景,只要“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我这心头,偏偏萦绕着一件最大的“闲事”,如茧自缚,如影随形。直至那《落梅花》的笛声破空而来,方惊觉:执念之深,原是因为不肯承认——有些等待,本身即是相逢。
夜更深了,风里似乎传来隐约的笛声,呜咽着,是那曲《落梅花》么?“玉笛谁家,吹彻清商落梅花。”笛声如丝,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从心底最深处牵扯出来,悠悠地,在眼前浮动,直叫人思欲醉了。
不知何时,那天边的墨色,竟淡了一丝,透出些许瓷器般的青白来。长夜将尽,我这一番无用的羁留,也该散了。归去罢。晓风拂面,竟带了些许温润。纵然音书难通,万里相隔,但总有一个念想,如同那云巅茶舍里一杯永温的香茗,在等待着。远山轮廓渐渐清晰,恍若墨迹未干的邀约。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穿过千山万水,轻轻地说:
“三春好景莫徘徊,会饮明前茶一杯。且上云间茶社里,我烹香茗待君来。”
我缓缓直起身,离开那浸透了夜凉的栏杆。心底里,竟也生出一点微茫的、属于自己的豁达来——“倘若老天怜一念,云巅坐看日归家。”

(张毅龙,湘人,曾务农、做工、执教,诗文散见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