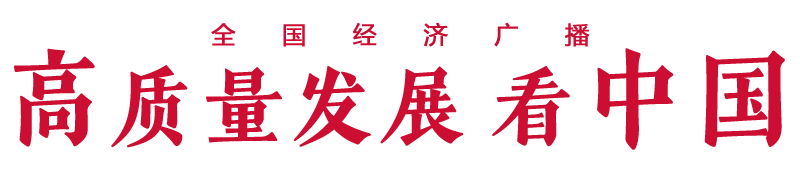科技发展的今天,13亿人口的中国中仍然有6亿多农村地区的劳动人民依旧做着最传统的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刀耕火种”,盼着家里的孩子能够出息走进城市,给全家带来希望……
20年前,四川宜宾人罗强不顾父亲反对,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父亲3年未与他联系——因为父亲希望儿子能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不是仅仅在城市打工。20年后,当罗强携妻带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时,父亲再次被激怒,坚持要分家断绝关系:“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罗强与父亲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上的差异与分歧,不仅是两代人代沟的体现,更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与交锋。罗强的遭遇生动地说明,“新型农民”返乡创新创业不仅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限制,也会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着困境。更为关键的是,“新型农民”在当下还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可能会承受家庭的压力和旁人的非议。
虽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重点工程,是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有中国特色农民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但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通过升学、经商等路径跳出农门,不仅是农民到市民身份标签的置换,还是生存生态的根本性改变,实现了人生突破和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罗强父亲看来,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儿子“人往低处走”;这样逆向的社会流动,不可避免会影响罗强一家的“脸面”。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之后,罗强对情感厚度和精神家园有了更高品质的诉求。在乡愁、亲情、友情的驱动下,罗强试图通过“新型农民”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同群体的交流、对社会的融入。只不过,他却面临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是一种生活在农村、收入低、素质差的群体,是贫穷的“身份”和“称呼”,而不是可致富、有尊严、有保障的职业。
窗体顶端
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职业农民则充分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理性选择使利益最大化。“新型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个职业属性;将“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划上等号,认为“新型农民”没有出息、没有前途,这样陈旧的价值观念,显然比时代潮流“慢一拍”。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号,让他们有尊严、有收益、多种田、种好田。要通过规模种植补贴、基础设施投入、扶持社会化服务等来引导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在政策上必须要从补贴生产向补贴“职业农民”转变,在制度上必须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制度”,科学设置“新型职业农民”资格的门槛。
那些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农家子弟返乡创新创业,既需要公共部门提供“制度补血”,也离不开社会认同的支撑。“新型农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倒退,从本质上则是对成功路径多样化、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的探索和尝试。吸引更多的农家子弟回归乡土世界,固然需要乡愁、亲情、友情这样的情感纽带,也离不开农村发展空间的支撑。
像罗强这样被误解的有志青年并不在少数,政府需要加强对“新农民、新农业”宣传及引导。当然,6亿多人口的农村现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我们只能希望“新农民、新农民”的改革风早日普及,让罗强这样的青年不再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