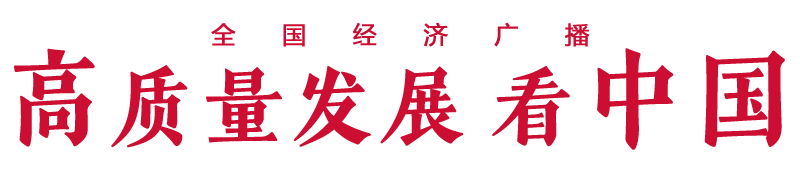我相信,诗意的旅行,也就是本书的标题,点明了绝大部分南宋画院和院体风格点景人物山水画的主题。若干年前,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提交的一篇题为《髡残和他的题跋》的文章中,曾提到这位清初个性派大师的画作是如何与他画上长段的诗句题跋相并行,二者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四阶段的叙述:虽在题跋中交代得更为清晰,但从绘画上也能阅读出来,就像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幅作于1663年的作品,其主人公——在此是一僧人,但他同样可以是一个文人、诗人或退仕的官员——在自然中隐居;时不时外出旅行,带给他感性的经验,滋养精神;他停下来休息,或站立观看,欣赏一些闲逸景致,或倾听什么声音;然后回到他安宁的茅草屋中。我演示了这一顺序是怎样帮助我们阅读髡残的绘画。重要的一点是,同样简明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构成了一种理想的四段式叙事,大多数,或许是绝大多数南宋院体点景人物山水画,都可以按此划入四种阶段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表现隐居生活的画面,这在南宋册页中不计其数。有些表现得非常直接,就像一开佚名画家的册页,其中的“隐士”坐在开敞的房间里,出神地望着他假想中的拜访者。其他的画则表现得更为微妙,常常只表现仆人在湖边别墅外等待,有一位友人前来造访。在中国,隐居也可以相当社交化;这些画中表现的人物常常并不是真正的隐者,而是从城里外出在水边别墅度夏的文人士大夫。在他们心领神会的这类画面上,根本就不必出现隐士,而是用山径、桥梁、城门等暗示其居所;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幅扇面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自然中逃遁,我们的诗人、文人逃避了外部世界的危险和污浊,仍能保障他最基本的人际交往。
但是,转向不安稳的情况,如果隐居之士要获取新鲜的感受,引发抒情的兴致,丰富他的生活并寻觅作诗的素材’他就必须外出行走。这种情形在另一幅佚名画家的扇面上被微妙地表示出来:一条小路将观者的视线引向悬崖下一处隐者屋舍,然后又通向无保障的远方。在有夏珪署名的扇面上,一个人走过了小桥,站在路的一端,仿佛不知所措,望着晨雾,考虑着是否要继续前行,而他的仆人则在屋前洒扫庭除。
继续往远处行走,这类绘画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各种要素构成的画面,使观者可以有序看到一次旅行的过程或者在旅途中遇到的事件。通过画面近处右下角一条小路的指引,我们可以看到游人和他的随从已经走近客桟,客栈外挂着旗帜;他们停下歇息,吃饭喝茶,或住上一宿,然后接着上路,把我们再次带到画面的纵深之处。弗利尔美术馆藏的有12世纪画家阎次于落款的册页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另一幅画上有一位不出名的小画家吴叔明的签名,其描绘的歇脚点则是佛寺。这三幅册页都是李唐的第一代追随者的作品,而李唐本人像是专长于这类图像的制作。
由佚名的二流画家创作的这类题材的变体,包括一幅扇面,一位醉客骑在驴背上,正在接近坐落于花树丛中的小客桟;而另一幅扇面上,一位官员正在匆匆上路前休憩。行旅的描写可以是为公干或其他严肃的差事,也可以是为了唤发诗兴。
另外一些行旅图,典型地按照范宽的传统绘制,主题是表现旅途中走过雪山关隘的艰难。波士顿美术馆藏传为范宽的扇面就是这样的例子;另一幅佚名画家的扇面用的是相似的图式:行人正在接近一家客栈,而路径依然蜿蜒向前延伸。这类作品的存世杰作之一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梁楷的作品,两位骑着马、身着冬衣、头戴皮帽的行人走入北方神秘山谷,走向一个城门,将要通过关口。另一件几乎无人知晓的有同一画家签名的斗方表现了与之连贯的画面:同样的两个行人,已经穿过山脊,走下被雪掩盖的桟道。至于梁楷如何能够在其他作品中继续这个题材,发展出一种在更宏大的画面中更特别的叙述,我们只能空自存想了。
在杭州地区,以立轴形式来表现行旅的情况,在当时可能和扇面册页一样流行,但是它们并没有吻合后期中国收藏家们的趣味,所以只有极少数存世,而且主要保留在曰本。京都金地院和光影堂收藏了三件13世纪佚名画家的杰作,它们出自一套描绘四季的组画,表现了一个更大的场景,这是由于文人容忍度的局限而造成这些绘画大量散失的又一例证。这些画上的行旅者体验到的不是艰难,而是由自然唤起的强烈的审美感受,以及倾听到的天籁之声:夏天阵雨过后,瀑布上方的枝丫上传来阵阵猿鸣,吸引行旅者回头观望。就像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所作的德国浪漫主义绘画中出现的“背影人物”,他们在沉思观看景物的经验,超越他们的是那些与“驻足的旅者”相呼应的被观看、听到和感觉到的事物,这样的人物形象占据了欧洲此类绘画以及浪漫主义诗歌的中心位置。
还有,像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一样,创作这些绘画的南宋画家采用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简约的再现技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章中介绍的,而且会在下面两章得到展开的一个观点是,在我的定义中,最好的诗意画并不取决于艺术家本人的抒情程度——尽管我们也应考虑这一点,只要它不与文人士大夫身份扯上关系——而是依赖于完全掌握了某种再现的技巧,以看似轻松的方式,来表现空间、气氛、光亮以及物象表面的细微和转瞬即逝的效果。这些自我克制的画家掌握了这套本领,就不必用力去强调再现的效果,他们减少了对细节的刻画,柔化和简化了形式,以看似简单的形象在观众心中唤起深情的共鸣。
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绘画的效果最好地回应了唐诗中的同样努力,就像宇文所安和余宝琳所说的那样,能够通过“只让感性的形象来体现观念,没有枝蔓的解释”,而把“物的世界和情的世界”结合起来。当然,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其不同在于,绘画中的形象无法诉诸直接和清晰的感情陈述,如同它们在诗歌中那样(但在实践中也不尽然),结果是,它们对应了怎样的“情的世界”只能靠推测,通过与之相关的比喻和其他含义来进行阅读。在绘画中,这样的形象与感情的结合一旦被滥用,就很容易变得表面化或枯燥乏味。
于是,我们发现,特别是在诗之旅的第三个阶段里,行旅者停下来,体验景物些特别的细节。大量的重复性使得许多这类作品不再抢手。在京都金地院和光影堂收藏的一幅秋景人物图上,行旅者在松树下坐着歇息,对着黄昏中两只在天空盘旋的仙鹤沉思;画家在程式基础上做出的变化,以及笔法的流畅肯定,把该作品从枯燥乏味中解脱出来。但作为一种类型,这样的作品不计其数,文人雅士坐在松树下赏月,或仅仅目击虚空,或站在落瀑前沉思,面对如此众多的作品,我们真希望他们还能干些别的什么事情。诗句能对具体的人物活动作出区分,但绘画却很难。这样的重复现象损害了南宋院体风格绘画的声誉,尽管我希望读者现在已经能够相信,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敏感性或是新鲜感方面,院体画都不输于文人画。
还有,一个画家,只要具有梁楷那种敏感性,就能摆脱俗套’重新构思情节,避免直白地去描绘一处景观或声源,以吸引其漫步者的注意:行吟诗人非常简明地成为画面的焦点,身边的洞穴传来声响,凸显但又神秘消失的悬崖压在他的头顶上。由于无法获得对这幅画面的清晰解读,我们在这位行旅者身上感到某种不安,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和感受的一种投射。另一幅从未发表过的册页,有梁楷的署名,也证明他的确是一位简笔画大师。在雾气弥漫的河岸,一人泊舟其旁,头枕船桨,横卧舟中,吹笛自娱。这里,诗意的漫游接近尾声;或许,若有一首诗句作为对开,这幅册页会显得更稳定。我们的文人诗人占据了自然中的宁静之处,躲避其中,只要待在那里’就可以无忧无虑。
我们关于理想化叙述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旅行者返还家乡或隐居地,回到安宁的环境中。在一天或整个行程结束后到达了休息地,大致是相同的意思,这体现在许多画中,尤其是马夏一派的作品中,观者常会看到回家的村民或渔夫正在抵达他的茅屋。典型的情况是,人们看到他将要走过木桥,像在出游的画面中一样’这些常常是对称的,标志着外部世界与内部隐蔽之所的分界。波士顿美术馆藏有马远落款的著名的《柳岸远山》,是这一样式的代表。这个题材更多与夏珪有关,他比任何一个画家更能创作出这种具有静谧、迟暮和怀旧感的归隐模式。他究竟怎样做到这一点,很难进行分析,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在这类图像上,当归返的形象是村夫而不是文人时,更加强化而不是淡化了画面的怀旧感,因为渔夫、樵子、牧童和农民的作用,如我在别处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欧洲的田园景象,代表了一种过去的、不可回复的阿卡迪亚式的质朴单纯。在那里,具有文化教养的观者会想象他自己融入其中。在一幅不太知名的有夏珪落款的扇面上,关于一天结束的主题与岁末的迟暮感联系在一起,一个农夫在寒冬中走近他河边的屋舍。王维和其他盛唐诗人在诗中频繁描写回家的主题,夏珪同样用这个题材表示“回归到那些本质而自然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理想化地描绘了乡村景象的图画仅仅是为了那些梦想田园之乐的人而作;隐居图画的观众,除了在他们的想象中,很少会真正采取隐居的方式;旅途的艰辛和收获是由那些可能足不出杭州的人所欣赏,至少出自他们的意愿。在此,我们可以再做设想,这样不协调的关系可能会削弱关于绘画的信念和“真实度”但在今天没有人会那样想。郭熙以他的观察,指出一种更接近于真实的理解方式,山水画是为了满足那些“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者的需求,因为“渔樵,隐逸所常适也”,也是为那些因为家国之事而滞留城市的人而作。我关于南宋院体诗意画的论点和郭熙相差无几:对于那些能够得到并欣赏它们的人来说,诗意画舒缓了生活的现实,它们唤起一种优雅和谐的诗意经验,呼应了人们对远离尘世、回归到无优无虑的大自然等这些由来已久的理想的深切渴望。
我们可以用波士顿美术馆藏的一幅没有落款的册页来结束南宋末年的诗意之旅。我想,这幅画应该出自夏珪之手,但我却没有证据让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相信这个看法。秋江暮霭中,一人泛舟其上,将要靠近岸边。一条小路伸向树丛,并未交代舟子的归程,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片雾色。人们可以想象,对开册页上的诗句,记录了比绘画更明确的时间、地点以及舟子的思想和感受。绘画只能通过形式显现并为观众所见,这一限定阻隔了真正的通感;它能提供更多的暗示——感受风的吹拂、水的声响——但却不能像语词那样,命名和指称任何超越视像的东西。然而,它却能传达一种信息,通过空间,或者说(像在这幅画中)从清晰(实)到模糊(虚),有一种流畅感和直接性,这是一行诗(“步入烟霭中”)所不能相比的。绘画还能够以有限和暗喻性的方式,传达时间的信息。傅汉思在谈到本章一开始所引王安石描写江景时说的“图画难足”时,认为这句诗“暗示了……诗歌能做而绘画所做不了的;例如,眼前的景象中会涵盖对过去景物的观看”。尽管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一个有足够技巧和敏感性的画家能够画出,如南宋画院大师所作的那样,一种暗示的过去,通过时间和迟暮的形象,唤起一种无所不在的怀旧感。
和这幅册页相配的诗句,如果真有一开的话,如果是同时代人的诗歌,而不是从某首唐诗中摘录而来,那么它可能在原创性、敏感性或技术的含蓄性方面都无法和绘画相匹敌。如果说南宋宫廷的诗作趋于肤浅的话,那么那里的绘画,特别是其中精品,绝非如此。相反,南宋院体画的诗意境界和细腻感,从来不似那些诗篇,它们有无尽的能力来重新想象熟悉的题材,把观众吸引到暗示性的、不确定的和未完成的叙述中。即使这样,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的章节中展开的,在此之后,只有很少一些画家,如一些晚明苏州的画家,以及日本江户时代的少数南画大师,特别是与谢芜村,追求相同的效果,并取得了他们各自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