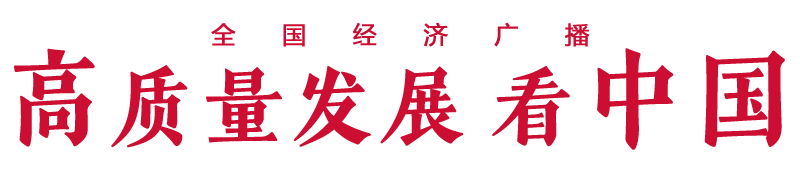文╱李福信
城市的霓虹灯里,有灯红酒绿,有旖旎风景,有沉浮起伏,有曼妙风尘。
那璀璨的霓虹灯里,也有乡下的母亲,好奇,向往,羡慕,惶恐,百感交集的眼神。
一
周末的清晨,冬风凛冽,寒意逼人。
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小居里思绪翻飞,抚今追昔,不觉身入烟云,神出古今。
这样的日子,总让人想起些旧事来。
正巧看到四十年前在新宁县文化馆相识的文艺少年,三十多年前在新宁县高桥工商所相交的何石挚友,一位多年前就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军旅情怀、乡土情缘作家,发来的微信消息。何石问四哥,四哥那篇《妈妈的妈櫈》散文写得真好,可否放在家乡的《文化崀山》,作为卷首语?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相隔百里心意同,为家乡宣传,为亲情布道,为心灵放歌,当然可以的。

于是就想起妈妈的妈櫈,便起身下楼,到车库里去寻那张妈櫈了。
车库里的光线有些暗,灰尘在从门缝漏进的光束里缓缓游动。妈櫈就立在墙角,静静地,像在等待着什么。櫈面上的木纹一圈一圈地漾开,像是鲤溪的水波,又像是母亲额上的皱纹——那些皱纹啊,是岁月的涟漪,一圈圈地荡开去,荡漾成了四哥整个的童年。
何石在微信里说,四哥的文字里有乡土的气息,读着读着,便仿佛在与自己的母亲轻轻对话,在与人之初性本善的真情细语。
这话说得真好。人生奔走的原野上,谁不需要这样一张妈櫈呢?需要那木纹般细腻温润的心灵,需要那样一个可以安然坐下的角落。
于是便想起,再过半个多月,就是母亲九十五岁的生辰了。虽然她已经走了十七年,但生辰总归是生辰,是要记着的,便想写点什么。
那就写一篇《城市的霓虹灯》吧,记念那个第一次进城来的乡下母亲,记念她在闪烁的霓虹灯下,那张惶恐的、羡慕的、好奇的、向往的,各色神情交织,温柔而又沧桑的脸。

二
从文说道,乡愁总是美丽的。
冬风萧瑟,寒气横流,已是深冬了。冬月总是让四哥无法忘怀——母亲在冬月里来,也在冬月里走。生与死,竟都在这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了。
前不久在香港,偶遇了旧友尔康。两人坐在茶餐厅里,看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说起了许幻园,说起了李叔同,说起了“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说起了那个仁义礼智信还被人珍视的年代,说起了因为慈悲所以热爱、愿与君同奔赴山海的人生。说着说着,便觉着而今的人世,真如灯蛾扑火一般,欲望无穷无尽,火不灭,飞不止,孜孜不倦,生生不息。非要到了一定的年岁,看懂了,看透了,才什么都舍得起,放得下了。
这个世界啊,当寺庙的香火在二维码的扫描声中缭绕,当中小学校门前立起三角钢架水泥石墩的屏障,当俄乌交战的夜空被硝烟染红,才恍然发觉,所谓的太平盛世,原也不过是过眼烟云。风花雪月,人生际遇,到头来都成了记忆里的碎片,闪着幽微的光。
然而,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些记忆是清澈的,像鲤溪石缝里流淌出来的山溪水,汩汩地,漫过山野,漫过心田。
三
还记得那是二00五年的冬夜,母亲第一次到邵阳来看四哥。
那时的车站是灰扑扑的,灯光昏黄如豆。母亲从长途车上下来,手上提着个竹篮,沉甸甸的,里面装着腊肉、血粑、晒好的红薯干——都是鲤溪老家的土产,都是四哥和孙女最爱呷的。她的头发在灯下闪着银丝,眼里的光却比车灯还要亮些。
走在街上,母亲紧紧攥着四哥的衣袖,手心里有汗,湿湿地。夜幕正一点点垂下来,街道两侧的霓虹灯渐次亮了——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像是谁打翻了颜料铺子。那些光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晃晃悠悠的,成了一条流动的河。
“四伢”,母亲停下脚步,仰着头,看百货大楼上闪烁的招牌,“这些灯,怎么这么多颜色?还一闪一闪的,不费电么?”
四哥笑着解释:“这是霓虹灯,妈妈。城里晚上也做生意的。”
母亲摇摇头,喃喃地:“在鲤溪,天黑了就点煤油灯,省着用,早早睡了。这里的天,好像永远不会黑一样的。”
带她去三八亭的“五千年”餐馆吃夜饭。餐馆里热气腾腾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母亲却局促着,不敢坐那张红木椅子,直到四哥扶着她,才慢慢地坐下。火锅端上来,热气模糊了她的脸,那些被岁月刻下的皱纹,在蒸汽里显得柔和了许多。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猪肉,吹了又吹,才送入口中。
“不如自己屋里喂的壮猪。”她轻声说,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这汤好喝。”
回去的路上,母亲依然仰着头,看那些变幻的光。她的侧影在霓虹的映照下,时而泛红,时而染蓝,像是四季在她脸上流转。
经过一个橱窗时,她忽然停下,呆呆地看着里面一件枣红色的毛衣。
“真好看。”她说。手指在玻璃上轻轻划过,却又像被烫着一般,迅速收了回来。
四哥说:“妈妈,我给你买一件吧?”
她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我在屋里穿什么新衣裳?做事情不方便。看看就好,看看就好。”
那一刻,四哥忽然明白了她眼里的光——那是好奇,是向往,是惶恐,是羡慕。城市对她来说,就像这霓虹灯,美丽,却遥不可及;明亮,却不是自己熟悉的鲤溪。
……
四
多年后,母亲病重,四哥带着母亲,又来到了四哥所在的城市。
医院归来,母亲躺在华龙宾馆的床上。窗外依然是城市的霓虹灯,二十四小时不知疲倦地闪着。她已倦怠说话,只是偶尔睁开眼睛,久久地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
有一回,她忽然轻声说:“像……像鲤溪热天里的萤火虫。”
四哥怔在那里,泪便下来了。
是啊,鲤溪的夏夜。那时母亲还年轻,四哥还是光着脚丫满山跑的孩童。夜幕降临时,满山谷的萤火虫便起来了,点点绿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是星子坠落凡间。母亲常坐在家门口的妈櫈上,摇着蒲扇,四哥兄弟姐妹便追着那些小光点跑,笑声在山谷间荡来荡去。
“莫跑远了,小心仈倒(摔倒)。”母亲总是笑意盈盈地喊着。
偶尔,她会讲起外公嗲嗲外家阿姆的故事,讲更早以前,崀山的七星桥和鲤溪人如何在山间开垦,如何依着鲤溪建起家园。她的声音温柔而平稳,和着溪水潺潺、虫鸣唧唧,成了最美的夜曲。
那些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却是温暖的,真实的。不像这城市的霓虹,虽绚烂如昼,却总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触不到,摸不着。
……
五
母亲终究是回鲤溪去了,长眠在老屋侧旁的白家冲。那里没有霓虹灯,只有四季轮回的光景——春有杜鹃染红山,夏有萤火点夜空,秋有明月洒溪涧,冬有霜花凝窗穹。
如今,在她九十五岁生辰将至的这个冬夜,四哥站在阳台上,远远地看着这座城市的灯海。那些霓虹依旧闪烁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交织成一片人世间的银河。但在四哥眼里,它们渐渐模糊了,化作成另一番景象——
那是鲤溪夜晚的点点灯火,从散落山间的土屋里透出来,温暖而稀疏;那是煤油灯下母亲缝补衣裳的身影,针线在她手中变戏法样穿梭;那是灶膛里跳跃的火光,映着她被岁月雕刻的沧桑老脸。
“妈妈”,四哥对着夜空自言自语,“城里的霓虹灯越来越多了。可我最想念的,还是冬天的风雪夜里,你带着我们,娘娘崽崽围坐在火柜里,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光景。”
一阵冬风吹过,带来城市特有的气味——汽油的,灰尘的,远处餐馆飘来的油烟味。但在某一瞬间,四哥仿佛嗅到了鲤溪冬夜的气息:柴火烟味混杂着霜雪的清冽,还有母亲挂在灶台上熏制的腊肉香。
六
十七年过去了。母亲的妈櫈依然立在车库的角落里,櫈面上的木纹如水般流淌,记录着无数个鲤溪的日夜。四哥走过去,轻轻抚摸着那些浸润着母亲芬芳的纹路,就像小时候抚摸母亲劳作后粗糙却温暖的手。
城市的霓虹灯依旧在窗外闪烁,不知疲倦地向夜空诉说着人类的繁华。但在四哥的心中,永远有一盏灯,比所有的霓虹灯更明亮,更温暖——那是母亲煤油灯下的微笑,是鲤溪夏夜的萤火,是乡愁里最美丽、最永恒的光。
冬月十五就要到了。

母亲,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也有这样温暖的灯光相伴。而在这边的世界里,你的四伢会永远记得,真正的光明不在城里的霓虹灯,而在你带着四伢在鲤溪的那些简单的岁月里,你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点燃的,照在儿子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心灯。
夜深了。远处的霓虹还在闪烁,像是这座城市的脉搏,一下,一下,跳动个不停。
而四哥,在这个冬风凛冽的夜里,想起了鲤溪,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些萤火虫般,明明灭灭的往日时光……
(李福信,新宁县崀山镇鲤溪人氏,毕业于武汉大学。邵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府侨办主任。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国内各级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