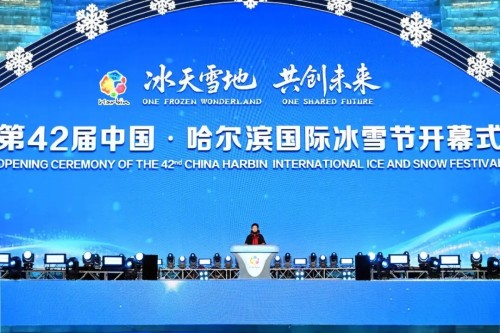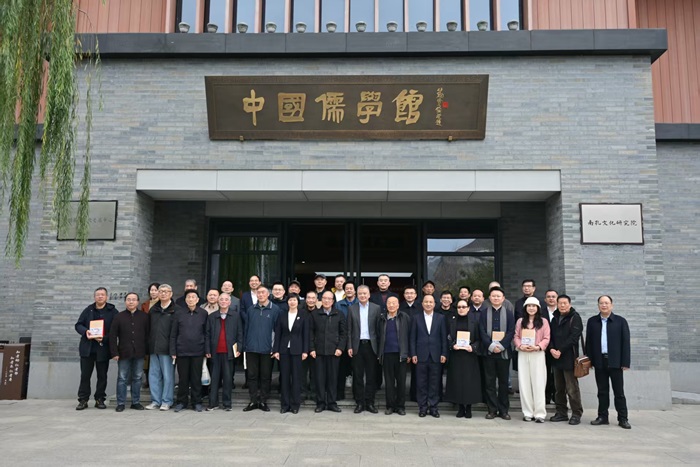文/张毅龙
这满城的华灯,原是盛世的眼睛。可我的魂,偏被一扇素简的窗棂勾了去——那光晕温润如隔世的玉,在万千璀璨里,守着豆大的清明。

茶烟起时,白日清谈的余韵便漫上心头。半窗明月移过阶庭,茶烟袅袅散入虚空,恰如此刻墨痕在宣纸上走成孤舟。俯看街巷,车流是镀金的河,而我的小窗,恰似一枚闲章,轻轻烙在喧闹的边角。
灯火深处,藏着人间的暗语。写字楼的蓝光屏还在闪烁代码,外卖骑手的尾灯在街角划出流星弧线。广厦玻璃切碎月光,阳台上老母亲晾的衣裳在风里摆成旗语。少年吉他声撞上霓虹,碎成带颜色的雨。这些光啊,有的在催赶明天,有的在打捞昨天。直播间的美妆灯彻夜不熄,而我只守这半窗月、一杯茶,在葭浮才一日的须臾间,生出无涯的芳思。
恍然间懂得古人心境。杜甫在煌煌灯烛里看见“寒裳赴前程”,白居易守着青灯听见“幽独赖鸣琴”。这思绪牵着我,回到独坐小舟的午后,苇蓬漏斜阳,半日未过江。唯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窗——原来我们怜惜的,从不是寒微本身,而是寒微中那颗不肯随波逐流的心。
夜更深时,楼对角的咖啡馆打烊了,最后一盏灯像星星眨了最后一次眼。而营盘路书店的光晕,正哺育着夜航的灵魂。这是盛世的慈悲——总有些光,不为炫耀,只为等候。就像地铁末班车里,那个戴着降噪耳机读诗的少年。
我关掉台灯,小窗却更明了。月亮从楼宇峡谷浮上来,清辉与灯火在窗台和解。目光垂落处,望着办公用的紫砂杯,杯沿灰痕如岁月印记。蓦地,四十多年前离乡的清晨扑面而来——母亲塞进书包的烤红薯早已化作故土的温度。先生乡音诵读的“知我者谓我心忧”,直到今日才尝尽滋味。
记忆的河流继续回溯。初入公廨这座大楼时,新衬衫领子磨得脖颈生疼。文件堆里斟酌词句的深夜,“蜗角虚名”让脚步沉重。直到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热饮柜前,看见加班同事对手机镜头练习微笑,耳畔忽然响起父亲说过的那句:“心底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就在这一念回转间,原来“云在青天水在瓶”,是在琐碎日常中认出本心。当参与推动的“优质均衡”计划落地,站在新校舍前看见那些举着平板电脑学绘画的笑脸,那个瞬间突然明白:所有走出大山的跋涉,都是为了更好地回到精神的原乡。
收束思绪,整理完最后一件物品,相框里全家福静静躺着。母亲的笑容还停在送我上学的那天。智能手表突然显示心率异常——原是旧照片撞破了时光的结界。
手机响起老友邀约,说备了好酒。我笑着应允,想起东坡“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今这山水,就在阳台新栽的茉莉里,在儿子用编程软件复原“春有百花秋有月”动画的声线里。
踏月归去,夕光正好。雨洗过的梧桐叶闪着细碎金光,像课桌上跳跃的阳光。共享单车的铃声响过,惊起一群白鸽,羽翼掠过玻璃幕墙,将云影写成天空的短信。
远山衔月,故园百里。今夜会有同样的月光,覆盖老屋瓦檐,照亮另一个少年带着无人机航拍家乡走出大山的路。而我只愿做那盏不灭的乡灯,在记忆拐角处,温柔注视每一个奔赴明天的身影。
毕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流水汤汤,明月皎皎,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盛世如海,万家灯火是浪花千叠。而我的小窗——这素简的、浸着龙井茶与电子书墨香的小窗,正是我泊心的舟。

作者简介
张毅龙,湘人,曾务农、做工、执教,诗文散见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