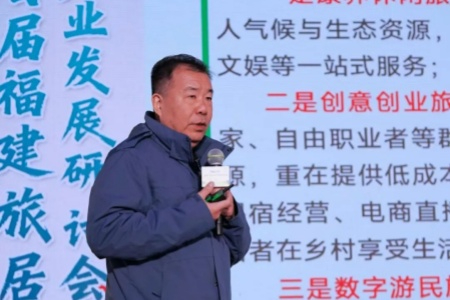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集体步入代际交接的关键时期。数据显示,未来十年,中国将有超过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传承问题,涉及资产规模达数十万亿元。然而,“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全球家族企业仅30%能延续到第二代,而传到第三代的比例更骤降至12%。在中国,这一挑战尤为严峻,娃哈哈、新希望、碧桂园等知名企业的传承过程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其中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爆发的家族信托纠纷,成为研究中国企业家财富传承困境的典型案例。制度缺失、规划滞后、法律冲突构成当前传承困局的三重枷锁,其影响早已超越家族内部范畴,直接关系到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念、企业稳定、科技创新乃至宏观经济健康。
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探讨中国企业财富传承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十分紧迫的一个话题。因此我说,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举办这个座谈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从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传承法律体系讲一些想法和大家交流。
国际经验 | 制度设计的传承智慧
洛克菲勒家族信托:财富永续的机制典范
1910年,约翰·洛克菲勒创立了美国首个家族基金会,开启了一套延续六代而不衰的财富传承机制。其核心奥秘在于通过制度化的资产隔离与分配规则,实现财富控制权与受益权的科学分离。具体而言,洛克菲勒将其90%的资产注入信托架构,规定受益人30岁前仅可获取分红收益,本金动用需家族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一设计完美平衡了“保障”与“激励”的双重目标:既确保后代生活无忧,又避免财富腐蚀奋斗精神。正如巴菲特所言:“给孩子的钱应多到敢做任何事,少到不能无所事事”。

在治理结构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双层制衡机制:专业投资团队负责资产增值,每年仅需提取5%用于慈善事业;家族成员通过理事会保留战略决策权。这种安排既保障了管理专业化,又维护了家族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其慈善投入绝非单纯的财富消耗——青霉素研发等投资项目不仅带来巨额回报,更赢得社会声誉与政策影响力,形成“献出越多,控制越多”的良性循环。百年实践证明,该模式成功抵御了遗产税冲击(美国遗产税率最高达50%)、化解了代际纷争,使家族财富从1910年的14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1.5%)持续增长至今日的300亿美元规模。
日本企业宪章:文化基因的制度表达

东瀛之地,百年企业数量惊人。金刚组历经四十代传承延续1400年,三井、住友等财阀跨越数个经济周期屹立不倒。其长寿密码深植于独特的制度文化基因:
单子继承制:彻底颠覆“诸子均分”传统,由长子或养子完整继承企业控制权。这一看似冰冷的制度有效避免了三星、澳门赌王家族式的内耗悲剧。日本民法虽在1947年废除长子继承制,但企业家为保护产业完整性,仍自觉延续这一传统。
家宪治业:三井家族1722年制定的《宗竺遗书》,经二百年演化于1900年形成《三井家宪》,其中“不得乘一时之机为急功近利而铤而走险”等训诫成为经营圭臬。金刚组家规更以“经商如牛垂涎细长,如牛行路步步扎实”的形象比喻,约束后代专注本业。这些宪章超越普通管理制度,成为家族的精神契约。
养子优才制:当血缘继承人能力不足时,日本家族企业开创性地通过婿养子制度引入外部精英。松下幸之助将企业交予女婿松下正治(原姓平田),后者带领松下电器成为国际巨头。这种以才能而非血缘决定继承的灵活机制,破解了生物遗传与人才稀缺的天然矛盾。
这些制度背后,是日本将武士精神与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融合:武士的进取精神推动商业开拓,儒家的“仁爱贵和”维系组织稳定。企业通过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实现“修身(员工培训)、齐家(单子继承)、治国(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正是这种文化制度双轨并进的传承模式,使日本企业在平成大萧条中创造了超过半数百年企业业绩持平或增长的奇迹。
中国困境 | 娃哈哈案例的深层剖析
信托失范:离岸架构下的法律冲突

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冻结令,将娃哈哈家族信托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宗庆后生前设立的离岸信托计划,因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陷入三重困境:
其一,主体错位。信托资产法定持有主体为建浩创投,但实际操作指令却通过娃哈哈集团财务系统下达,形成“信托账户企业化操作”的畸形模式。2024年5月,宗馥莉以“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为由从信托账户转出110万美元,彻底击穿资产隔离防火墙。
其二,权力真空。宗庆后去世前未指定信托受托人,导致宗馥莉自行获取账户操作权限。这种关键人依赖症使信托丧失独立性,蜕变为私人提款工具。
其三,权源争议。信托资金号称来源于“娃哈哈未来分红”,但集团自1999年改制后形成“国资46%、家族29.4%、职工24.6%”的股权结构。按此比例,若信托资产确系分红所得,则国资股东应得27亿美元,而事实是国有股东长期未获分红。这引发信托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
继承乱局:民法典时代的制度碰撞

家族内部,非婚生子女的认祖归宗之战折射出中国继承制度的深层矛盾:
身份认定困境:宗继昌等三人主张的婚外亲子关系,在抗辩间激烈拉锯。这反映了非婚生子女认祖归宗中举证责任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盲区。
遗嘱效力冲突:尽管2021年《民法典》确立公证遗嘱优先效力废除原则,但宗庆后是否留有合法有效遗嘱仍成谜。现实中,慢性病老人常因子女轮番照顾而被迫反复修改遗嘱,导致最终意愿难以确认。
情感伦理撕裂:宗庆后胞弟宗泽后公开谴责宗馥莉“不仁不义”,员工抱怨福利削减,家族内部分裂公开化。深陷家族企业治理泥潭的“过来人”李国庆疾呼“坐下来谈谈”的背后,是法律裁决难以弥合的情感创伤。
三重困境:中国式传承的结构性挑战
娃哈哈案例是中国企业家财富传承困境的缩影,折射出三大结构性矛盾:
制度供给不足:中国家族信托法规尚处雏形,民政部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仅千余家,且缺乏洛克菲勒式的专业治理架构。监管规则滞后使离岸信托成为风险雷区。
文化基因冲突:日本“家业至上”的继承伦理在中国遭遇挑战,均分传统与企业家“诸子争产”现实交织。当宗馥莉断然关闭兄弟工厂时,中国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企业治理发生剧烈碰撞。
跨境治理缺位:娃哈哈信托资金横跨香港、BVI(英属维尔京群岛)与内地,涉及法律适用冲突、跨境支付凭证残缺、离岸公司链条复杂。这种多法域监管真空成为跨境财富传承的致命软肋。
法律与制度优化路径
构建中国式家族信托2.0
基于洛克菲勒经验与中国现实,亟需升级信托制度:
治理革新:强制要求家族信托设立专业受托人委员会,纳入法律、财务及行业专家,建立“受益人30岁前仅享收益”的分配限制条款。参考日本家宪理念,将企业家经营哲学写入信托契约,约束后代经营行为。
慈善功能激活:允许慈善支出抵扣部分所得税(如美国),但要求公益支出比例不低于年度收益5%,并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鼓励设立教育、科研专项基金,培育社会资本反哺商业生态。
国资保护机制: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制实施年度可审计分红,明确信托资金来源审查标准。
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的二元分立
破解“传业”与“传财”的永恒矛盾,借鉴日本经验进行制度创新:
继承委员会制度:由家族长老、独立董事、行业协会代表组成继承委员会,提前十年启动接班人培养计划。对非婚生子女,设立胎儿权益保留份额机制,避免出生后诉讼。
职业经理人赋能:学习松下养子优才传统,建立“血缘优先、能者居之”的弹性继承规则。对家族能力不足的企业,推行李锦记家族基本法模式——家族成员需通过竞争考核方能进入管理层。
家族宪法本土化:制订《家族企业治理指引》,引导企业将“专注主业、控制杠杆”等理念写入章程。建立家族理事会与董事会联席机制,重大决策需双重多数通过。
跨境传承的法律协同
针对离岸信托困局,构建多法域治理框架:
跨境证据链管理:建立离岸资产登记备案系统,要求设立人保存BVI公司股权凭证、香港银行授权书等全套法律文件,避免“离岸黑箱”。
冲突规范优化: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增设继承章节,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减少平行诉讼。
司法协作破壁:推动与香港、BVI等辖区签订家族事务司法协助协定,建立DNA鉴定、遗嘱认证的绿色通道。
宏观经济影响与未来展望
传承风险的经济外溢效应
企业家财富传承绝非私事,其成败牵动经济全局:
就业稳定器:中小企业贡献80%以上城镇就业,传承动荡直接导致裁员潮。娃哈哈纠纷期间,多家工厂停产引发地方就业焦虑。
创新断代风险:日本研究显示,有序传承的企业研发投入连续性是动荡企业的3倍。中国科技企业传承断层可能削弱“卡脖子”技术攻坚能力。
资本外流压力:离岸信托乱象诱使资产跨境隐匿,仅2024年上半年,家族信托资金出境规模达600亿美元,加剧外汇管理压力。
制度创新方向
面向未来,中国需要构建具有文化适应性的传承制度:
儒家商道重塑:将日本“道德传家”理念本土化,提倡“仁信传承”价值观,工商联可设立“百年企业奖”引导长期主义。
数字治理赋能:探索区块链遗嘱存证、AI继承规划系统,利用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信托分配。
跨境传承试验区: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家族办公室自贸区”,允许境外受托人执业,建立离岸信托资产境内确权机制。
结语: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承制度体系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洛克菲勒的百年传承依靠的是制度而非道德,日本企业的千年延续根植于文化而非侥幸。今天,站在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集体交棒的历史节点,我们肩负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传承制度的时代使命。这不仅是守护民营经济的血脉延续,更是夯实中国经济基业长青的制度根基。
让财富在制度的轨道上传承,让企业在文化的滋养中永续——这应是我们共同致力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北京正义律师事务所于2025年8月10日举办的《企业家成长与财富传承法律风险防控座谈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