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春,萧红摄于上海鲁迅居所前
关于萧红的文学成就,研究者们各有所见,在此无需再论。为萧红的人生际遇敞开了另一扇大门的是她对绘画的学习和实践,这极可能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艺术思维的基础。
1935年,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由鲁迅协助编入“奴隶丛书”,而她自己设计了该书封面。封面简练醒目,中间斜线,直如利斧劈开,上半部似为东北三省之版图,“生死场”三字即印其上,寓示着山河破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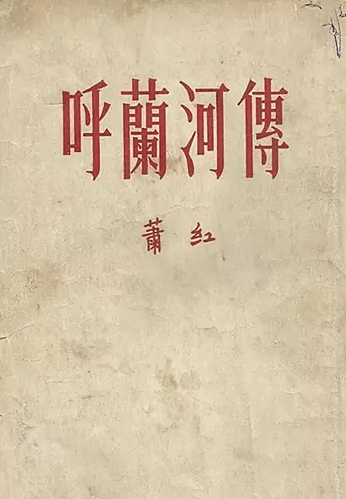
萧红作品《呼兰河传》
1938年,萧红、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同抵香港,先寄居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1941年初又挤住在乐道8号的小屋。在这里她写下最成功的回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小城三月》等。萧红在香港的绘画创作不多,比较典型的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马伯乐》的封面,这也是她亲自设计的。因为书中主角是一个出身优越但心态动摇、自卑的知识分子,封面也与这一主角形象相呼应,以右下角一个骑马的绅士型的人物图案做装饰,别有风味。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在香港期间,她还为端木蕻良等主编的《时代文学》(1941年6月至9月)制作过封面画。除此之外,萧红在香港的两年时光里,精神上的摧折与肉体上的病痛,似乎也并没有太多的精力与空间去从事绘画创作了。
但历史往往还会有出人意料的“脚注”,笔者近日就偶然查到,香港《立报》上曾刊载有三幅漫画,从署名、漫画内容与风格来看,都疑似萧红作品。就在1938年6月7日和8日,香港《立报》刊出三幅署名为“吟吟”的漫画作品。因为萧红曾用笔名“悄吟”,“吟吟”之名可能与之有关;此外,三幅漫画均反映了当时抗战军政与民生的急迫问题,也有可能与此刻身在武汉、处于抗战最前线的萧红有关联。
1938年,寄居在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虽几经犹豫与彷徨,萧红还是与同居了六年的萧军分手,5月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当年9月为避战火,又辗转至重庆。这两年时间里,她在上海、北京、武汉、西安、武汉、重庆各地辗转流徙,历经着抗战以来的各大主战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民生的艰难与惨淡,尽收眼底。而新近发现的这三幅“战时”漫画,所描绘的图景与蕴含的作者立场,与萧红上述经历是完全吻合的。
发表于1938年6月7日香港《立报》的两幅漫画,一幅被印制在头版的“左报眼”位置,一幅被印制在“花果山”副刊的版面上。应当说,同一期报纸安置同一作者的两幅漫画发表,在《立报》办报历史上并不多见。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纵观《立报》“报眼”漫画的主要特征,就是要针砭时事、聚焦国事。画面描绘了一架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飞机,机上飞行员正向一位降落伞中的日军飞行员挥手致意。显然,漫画名称打空格处的三个字应为“国民党”。这幅漫画实际上是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有所保留,或者说是在抗战军事上的消极心态。
而同期另一幅漫画,题为《血债!》,则更直截了当的体现了战区人民的苦痛。画面表现了一位中年男子,在空袭后的断垣残壁间,手捧幼子尸骸,失声痛器的情景。
1938年6月8日,香港《立报》“花果山”版面再次出现也是最后一次出现,署名“吟吟”的漫画。这幅名为《□□□□□》,题目被全部“打空格”,其画面内容更具讽刺意味,颇耐人寻味。画面中央站立着一位抗战士兵,他两手向外摊开,作无奈忧虑状;在其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分别画着列队而出的士兵,空空如也、结着蛛网的军费银库;写着“革命党”、“共产”字样的多支拳头,戴着种种面具、瞪眼咬牙的政客。这幅漫画,应当体现着当时抗战的国内困局,主要是指国共合作与资源调度的困局。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困局不解决,前线流血牺牲得来的战果,迟早将化为乌有;画面中央那位抗战士兵的忧虑状,正是困局中的生动写照。
三幅署名“吟吟”的漫画,在香港悄然面世之际,萧红还身处武汉前线。结合到她的文字风格以及先前的画作特征来看,“吟吟”极可能就是“悄吟”。此刻的萧红,已不再是孤身独坐于旅馆,在小纸片上随意勾画花纹的“悄吟”,而是要让更多民众知道抗战时局,已经颇有左翼文艺倾向的“吟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