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拯这部叙述唐代历史的书稿《历史不糊涂》,我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出生襄阳,曾隐居于鹿门山,有“孟襄阳”之称。一般将他冠以田园诗人,可是,我更喜欢他的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

李世民本想通过自己的挣扎,为千秋万代确立一个稳定的规则,能够让政治与亲情两全其美,让权力继承不再以骨肉相残作为代价。只可惜,他征服了广袤的土地,却无法改变文化的惯性。
这首诗,不是田园诗恬淡、悠远的意境,相反,是海阔天空一样的纵横捭阖。我想象,孟浩然站在岘山之巅,目光随汉水而去,俯瞰潮起潮落。他在看人事代谢,朝代更迭,历史兴衰。诸多感触沛然而至,这才酝酿而成高屋建瓴、气势恢弘的千古名句。
李拯与我是随州老乡,来报社不久就认识了。三十多年前,我刚入大学时随州还叫随县,隶属于襄阳地区。读他的书稿,想到孟浩然的诗,再合适不过。他的笔下,一个个唐代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彼此串连,衔接蔓延,呈现唐代由无到有、由胜而衰的全过程,多少历史感叹,尽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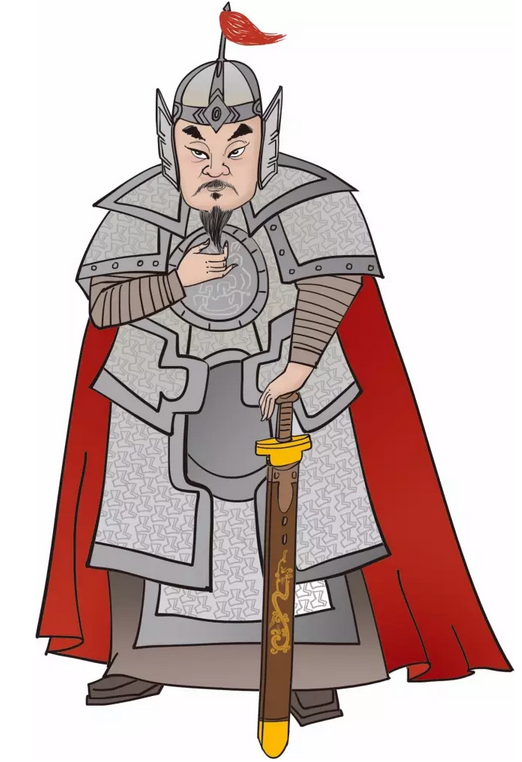
徐世勣善于在慷慨激昂的道德面具下进行着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他不像李林甫一类的人,在道德的外表下包藏祸心、口蜜腹剑,他不是卫道士,但也不会穷凶极恶,只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巧的是,报社里随州老乡竟有好几个,偶尔相聚,不亦乐乎。二〇一四年秋天,李拯与我坐在一起闲聊。他说起自己一直在阅读《资治通鉴》,对唐代历史颇有兴趣,想写几篇唐代人物,以人写史。
如他后来所说:“我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阅读《资治通鉴》的精神长征,每一次掩卷沉思,窗明几净之时,似乎总能感到历史从过去伸向未来的邀请,那些慷慨悲歌的人物所折射的时代问题,怎么与此时此地的语境如此相似?”写唐代人物,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李拯计划先写李密和李世民两个人。

武则天在一个男权社会成功实现逆袭,但当她登上权力巅峰时,却发现自己的权力难以在儒家秩序中传承下去。她成为了时间的弃儿,曾经打败了所有对手,最终败给了文化基因。
我建议他,不妨从一开始就考虑形成一个系列,先在杂志上开专栏发表,然后结集出版。没想到,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完成了十四篇历史随笔,一个完整的唐代兴衰史,在他的笔下得以呈现。
唐代历史,我知之甚少。小时候无书可读,回父母家乡枣阳,去乡下大姨妈家,二表哥手抄一本《说唐》,被我带回随县,看了一遍又一遍。知道了瓦岗寨,知道了长安,知道了隋唐十八条好汉。有段时间,每天讲他们的故事,还与小伙伴们比赛,看谁能完整背下十八条好汉的排序。

李隆基前半生英明神武,后半生自暴自弃,人生的悲剧,莫过于用自己的后半生彻底否定前半生。一代雄主的寂寞孤独冷,冻结成凄美的爱情故事,化作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
说起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头头是道。原来觉得秦琼武艺高强,结果只排名十六,想想觉得有些委屈。可是,十八条哪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从此,儿时心里,开创唐代的那些人物,个个都是传奇。
“文革”后参加高考,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上一位女同学颜海平,研究唐代,创作话剧《李世民》,一时轰动,并荣获全国戏剧创作奖。话剧上演时,大家都去观看,舞台上演绎的唐代兴盛,尤其令我们百感交集。“文革”浩劫刚刚结束,谁不期待百废待兴的中国,能够尽快走出历史阴影,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生活?

安禄山用“野蛮人”的淳朴作为掩饰,欺骗了所有自诩优越的“文明人”。他起兵造反,最后惨死在亲儿子手中,天道好还,诚不我欺。一切践踏道德者,必不得道德庇护。
唐代历史,这些算是最直接的接触,了解之肤浅,可想而知。直到李拯开始写作,我才有机会隔三差五地拜读新鲜出炉的作品。通过他叙述的人物故事,略知唐代兴衰一二,在我而言,仅此而已。
有意思的是,酷爱历史的李拯,大学本科并不是文史,而是理科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系。硕士考试时,他转换学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从此,现实观察与历史思索,与之相伴,须臾不可分开。

李泌辅翼三代帝王,他既梦想把世俗世界建成人间天堂,又渴望羽化登仙、遗世独立。他进则天下,退则山林,把入世的理性与出世的浪漫融为一体,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出世之心成入世之功。
其实,一个人,兴趣永远决定他最后的选择。读他下面一番话,可以体会到当他遥望历史时,心底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他的这番感慨,来自凝望北京潭柘寺的一棵千年古树:
人们在这棵树下冥想、祈祷或礼拜,寄托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有形的枝繁叶茂,而是这颗古树历经沧海桑田而积累下来的时间,是它经历的无数个夕阳西下、清风朗月和人事代谢。这棵古树,不过是变动不居的时间的一个具象的符号,而人们向古树祈祷,实际上是在向时间表达敬畏。
一个人、一棵古树,这样一个意象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人类精神的秘密: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

黄巢是历史的一个浪漫存在,一个激情四射的符号,他凭借“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拥有了穿透时间的魅力。只可惜,造反美学抵不过现实法则,黄金甲尚在,冲天香阵飘散如烟。
正是这种敬畏,才使李拯开始他的唐代历史之旅。在史料与故事的剪辑、呼应与映衬中,他思索人物命运,他追寻或许无迹可求的历史规律。十四篇文章,搭建成一本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架构。
与其他作者擅长讲故事的作品不同,《历史不糊涂》的要点不在于铺陈传奇,而是试图勾勒一个个唐代著名人物的命运,归纳某种性格走向。不同的性格,又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因传统密切相关,即便伟大如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人物,最终也不得不消弭于无形之中。
李拯谈到为何选择如下人物来贯穿整个唐代兴衰:
本书中选取的这些政治面孔,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续的连续体,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有唐一代的慷慨悲歌,李密、李世民、长孙无忌、徐世勣、武则天,代表了唐朝从建立到兴起的上升阶段,李隆基、李林甫、安禄山则活跃在唐朝达到巅峰而由盛转衰的转型时期,李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裴度则代表了一个衰败王朝力挽狂澜的努力,而李德裕、牛僧孺、宦官群体、黄巢、朱温则共同见证了唐朝的最后覆灭。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与唐朝的命运起伏息息相关,而他们的命运构成的轨迹,就像唐朝吐纳呼吸的脉搏一样,反映着这个王朝内在的政治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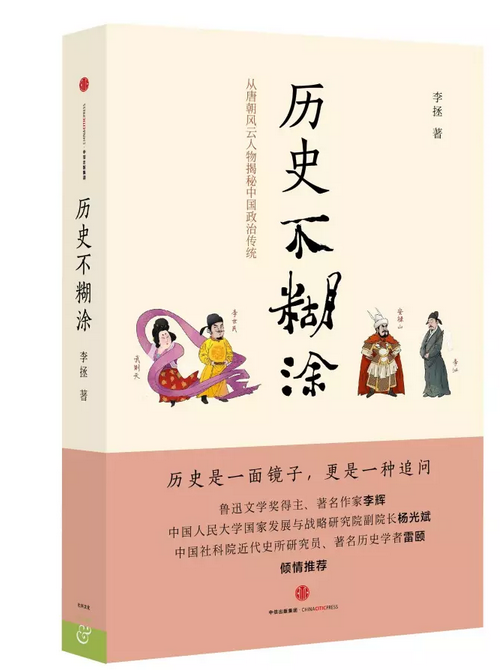
《历史不糊涂》书影,中信出版社出版。
研究政治学的李拯,在对唐代人物的叙述时,自始至终贯穿着难得的冷静思考。他显然是在有意识摆脱传奇的轨道,让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融入历史研究之中。是否准确,是否完整,并不重要,而在于,他必须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言之成理的归纳。在阅读本书之后,读者或许可以更深切地体会他发出的感慨:“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时让人不知所措,热爱它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迷恋它的激情澎湃、婉约清新,就不可避免地发出沉重的叩问:伟大而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以兴以亡的自我循环?”
对历史的敬畏,常常就藏匿于历史忧患之中。
总爱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历史更是一种追问。因忧患而叩问,因叩问而思考。
仰望历史天空,一个巨大的问号,醒目地悬挂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