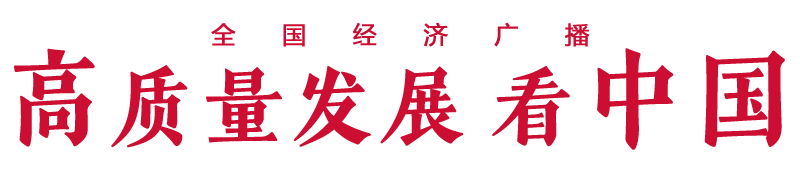曼梭醒寨另一独特风景是,当地人善采青苔,不仅自家食用,还用来销售。在江里捞取青苔,及时当地的风景之一,也是傣族人敬奉自然的一种方式。作为一门古老技艺,收取青苔虽然艰辛,但因为道法自然,它显现出让世人钦羡的自然美学。
一 罗梭江边的青苔 在那个早上醒来
曼梭醒寨的神树
后来我才知道,还没等我从景洪出发,青苔早就在那个清晨醒来。在二月的那个清晨,青苔已在曼梭醒傣寨边的罗梭江里,自然地醒来。
照傣家人的说法,清晨是佛祖传播智慧的时间。
青苔选择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此刻须先补上这一课。
罗梭江其实一点都不罗嗦,流水潺潺,清而洌。青苔醒来时,太阳或还没起床。青苔是一群欢乐勤快水灵灵的女孩,喜欢跳舞,不贪睡。它们知道,去大海的路也还远,赶路的江水从来不睡。夜深人静,青苔或会打个盹儿,睡一小会儿,但从不贪睡。
那時我还在去勐腊的路上。雾大车挤,我们中午才从景洪启程。沒想过,会有一次与青苔的不期而遇。罗梭江的青苔或许早就了然这一切,不知是不是有些神性?
说青苔在那时醒来,并不怎么恰切。世人正在酣睡,世界正在酣睡,青苔倒一直醒着。西双版纳的冬日温熙如同阳春,但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寒潮凶猛,版纳也冷过几天,早晚气温只有几度。那天的雾真是很大,大过了山,大过了江。澜沧江上雾气蒸腾。大雾把傣家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一起严严实实地包裹起來,就像包裹一個嬰兒。青苔比婴儿更婴儿,深藏于罗梭江的江水里,任何一点轻微拂动都难敌它触觉的锐敏。我猜它笃定感到了霧在河面的拂動。雾是不是从江面升起的,青苔不知道,江面以上的纷纷攘攘灯红酒绿,它从不关心,关心的只是身处其中的江水。但它知道,雾对江水的拂動,和一只水鳥偶尔划过河面又蹦又唱弄得水花四濺的搅挠,完全是两回事,雾轻柔得多。雾的脚,或是用来跳芭蕾的。
这样的季節,通常都是雾的天下。
从头年十月,到次年四月,西双版纳正值旱季,干燥,有些年头几乎滴雨不下。恰在这时,大雾漫了起来,大地一片迷蒙,空气变得湿润。前些年,当整个云南让干旱折磨得几乎奄奄一息时,白桦先生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忆旧,说他五十多年前在西双版纳时,大雾常常直到中午才慢慢消散。诗人公刘在一首诗里浪漫地写道,哨位上的值勤士兵,可以扯把浓雾擦擦刺刀。没人追究一团雾是不是真能擦亮哨兵手中的刺刀。如今,雾似乎比以前小了。但小了些的西双版纳的雾,那种真正的雾,依然很大。上天悲悯。雾是对西双版纳的旱季,对那种干燥酷热的一点補償,柔软而且湿润。
曼梭醒的青苔,就在那时的罗梭江里醒来。
都说岁月是时间之河,河里流的,当然就是岁月,是时间。时间无休无知,就像江水无穷无尽。人却不懂。青苔笑了,我猜。青苔笑了:人看似聪明,整天在忙,死忙活忙,却无法即时感受時間细微的流逝无声的抚弄,只会在时间过去之后大呼小叫,直到额头嘴角多了几道皱纹,才发觉青春已逝。青苔倒可以。常年棲居于时间之河中,青苔无惧甚至喜欢時間那种近乎游戏略带暧昧的抚弄。在这一点上,青苔的聪慧远甚于人。人娇气,怕火怕水,怕冷怕热。青苔不怕。无论冷熱四季,青苔都在水里舞蹈——那可能是一个湖,一条河,一片湾塘,或一泓淺水。
罗梭江的青苔更是幸运,世世代代都住在那条江里。罗梭江大名鼎鼎,我听說它已过去了好几十年。这条外界少有人知的江,从因茶而名声大噪的普洱流来,一路曲曲弯弯地流经景洪、勐腊,最终方汇入澜沧江的苍茫,一直奔向大海。罗梭江也因身在不同地方名字各异:在景洪市勐旺乡,叫补远江,在勐腊县象明乡,叫小黑江,在勐仑镇和关累镇一段,叫罗梭江,曼梭醒寨正好就在这段罗梭江边,江面开阔,水流舒缓。多年前我头次去过的,正是罗梭江环绕中的葫芦島。我在那里度過了一个神秘果一样神秘的夜晚。曼梭醒寨边罗梭江里的青苔是不是听说过葫芦岛和神秘果,我不敢肯定。那次在葫芦岛吃了一个神秘果后,再吃任何东西,不管酸苦辣麻,统统变成了甜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吃过新鲜的青苔后,味觉也会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