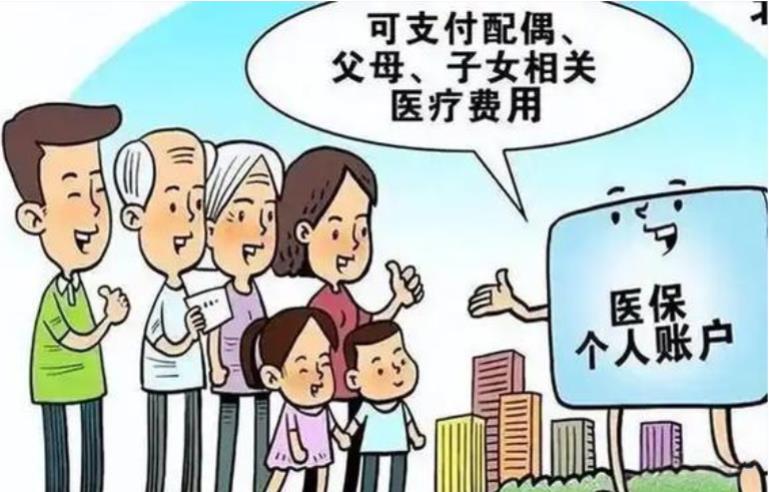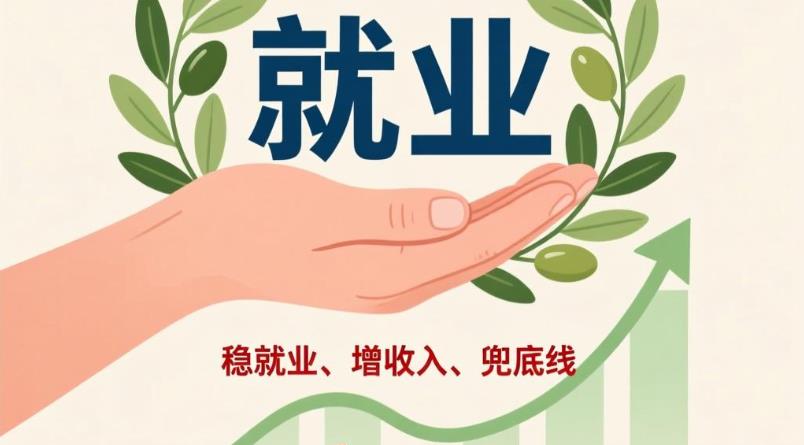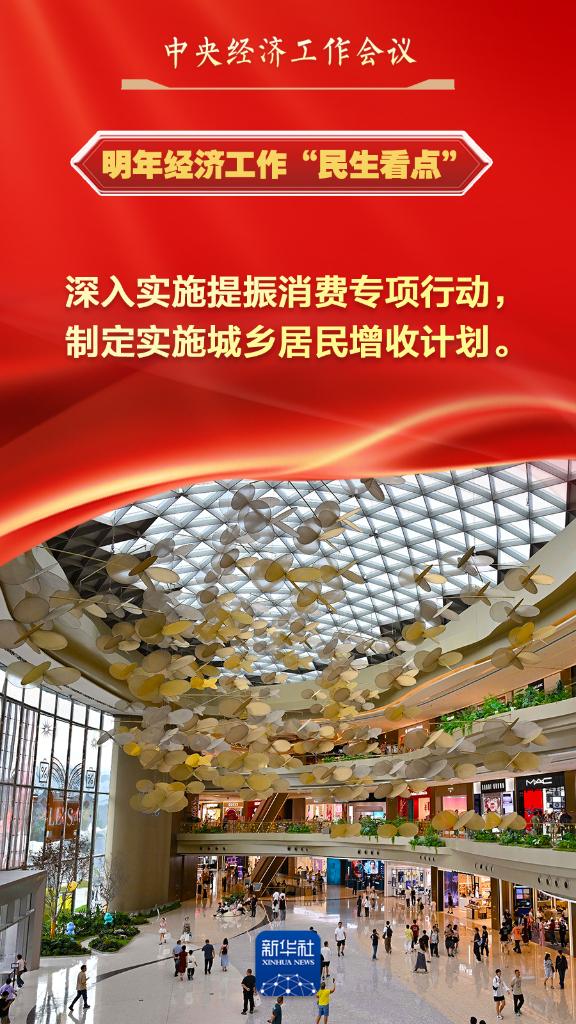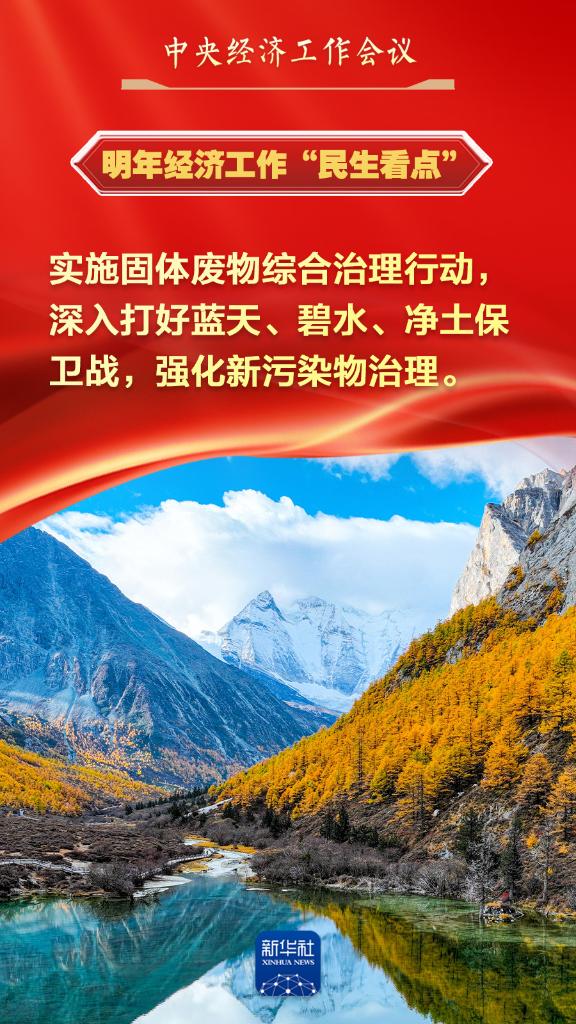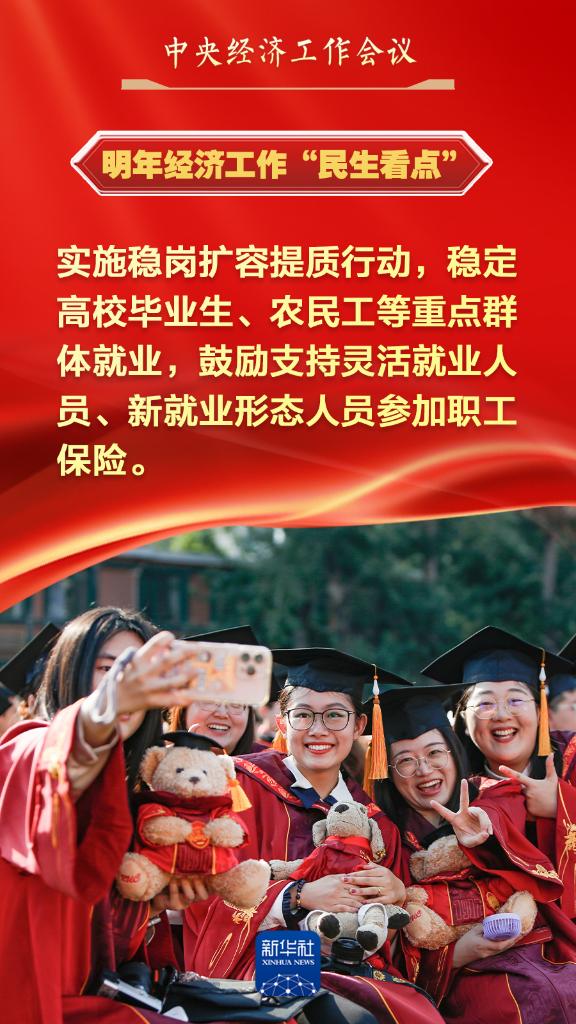罗宗强:1932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师从王达津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建立起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系统性地提出相应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界所推重。
罗宗强:我们当代人研究那些范畴,离开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倾向来谈,就说不清楚。于是我想到,解释古代文学批评的术语,必须了解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状况,所以我就放弃研究范畴,开始研究文学思想。在我看来,文学思想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和理解,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诉求,他们认为文学是什么,文学拿来干什么,什么是好文学。
我主要研究思潮,不是研究某个人的文学思想,而是研究整个时代,或者某个段落、某个流派,那种整体的创作倾向。比如说,唐代诗歌发展到盛唐以后,进一步发展好像已经不容易了,人们开始另寻出路,各种流派就出来了。韩孟、刘柳、元白,各种各样新的倾向出现了。到了晚唐,很多创作技巧已经高度成熟,再发展已经不容易了,就出现了李商隐、温庭筠,他们表达内心细腻的感受,追求深层次的感情表现。
在研究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文学思想的变化和政治局面、士人生存状况有很大关系,或者说跟士人的心态有关系。古代的士人,或者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他可能会有什么思想,这很关键。所以,为了把文学思想说得清楚一点,我又去了解古代士人心态,最早是研究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后来也研究明代。如果不把士人心态说清楚,文学思想就说不清楚,文学思想变化的根源也说不清楚。
实际上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多个方面有关,政治环境、社会风貌、生存状态、士人心态等等。比如说,明代为什么出现了许多世俗小说,像是《水浒传》《金瓶梅》这些。那是因为士人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影响,士人进入了世俗社会,市民的生活、市民的趣味影响了士人,导致创作倾向变了。到明代,什么都商业化了,就连民俗也商业化了。商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影响了士人,作品的趣味也就变化了。
实际上我研究士人心态,倾注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而喜欢看我写的书,我把他们视为知音,因为我自己也特别重视那些投入其中的感受。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那就难免是非褒贬,难免带着感情色彩。但是投入主观的情感,又必须以客观的材料作为依据,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同时用力,去体会、去贴近古人的心态。主观情感各人不一样,但客观材料是实有的,必须可靠。
我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很多事的评价。在当时环境下,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以此为基础,再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去领会那些士人的心态。有人评价这本书,说了两个字“悲慨”,在所有的评价里面这是我最重视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理解我的。
80年代中期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有几位年轻老师跟我一起做,我自己选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去年又出版了明代。周秦两汉过去由我的一个学生做,一直没有写出来。辽金元也有个学生做,现在快完成了。目前主要是差一个清代,原本有另外一个同志在做,后来他搞行政了,就没做成。我们知道清代东西太多,诗文、小说、戏曲全都有,目前要在国内找出一位这几个方面都通的,不好找。所以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就到明代为止。
我们说,从事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文史哲要打通,不单了解文学,还要能回归、进入古代那种知识体系,文史哲不分家。第二,他要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创作倾向变化了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要能看得出来。看过大量作品以后,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没有比较好的审美能力就判断不出来。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否则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只能客观地说现象,说不清楚原因。
一种文学思潮发展到另外一种文学思潮,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衔接、有过渡、有相互影响。后一种文学思想一定与前面的文学思想有所牵连,有意无意,有形无形,接受前面文学思想的某些优点。它可能在倾向上和前面的文学思想不一样,但是不能说不一样就毫无关系,即便相反也存在着衔接过渡的关系。所以我们写文学思想史,好多都是写过渡期。再一个,要注意不同地域文学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要把整体的思潮和不同地域的思潮梳理清楚。
我有个学生左东岭,他在首师大带了四五个人,搞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朝代更替之际文学思想如何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文学思想史研究我写到明代,没办法再写下去了,没有精力了。明代写了12年,写得非常辛苦,年近九旬,让我再写清代实在不可能了。文学思想史当作一个学科,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感到比较遗憾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套书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