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陈忠实不易。先生总体上是一个深刻的人,体验复杂,恰如其面。我难免想,先生对他的一些论者包括我在内,也许会窃笑,甚至要暗问:你究竟懂什么呢?
乡村陈忠实有一次自谑道:柳青在长安乡村从头至尾才十四年便传为风雅,我在灞桥乡村生活工作了五十年竟无人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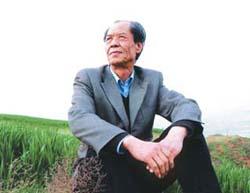
陈忠实
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情况有异,几近两类性质。不过乡村对陈忠实的意义是远远大于乡村对柳青的意义的。
古也罢,今也罢,在自己的家门口成事的人从来寥若晨星,因为羁绊太多,坠力太大。耶稣在拿撒勒传道不顺,遂往别处,孔子也周游列国十有余岁。柳青的家门口在吴堡,所以长安算是柳青的异乡,但灞桥却是陈忠实的故乡。陈忠实是在家门口取得功名的,由斯察之,陈忠实便有雄杰资质。
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西蒋村的时候,是无知无觉的,但他的父亲却有意让儿子离开乡村,到西安或别处去某一份体面的职业。父亲尽其所能,通常是变卖粮食和树木供给陈忠实和他的哥哥读书。很是艰难,不过终于读到了高中。毕业之前,陈忠实谨慎地为自己谋划着,当然,已经二十岁,他也能够这样做了。他的打算是:上上在大学深造,其次当兵,其次回乡村。遗憾当年大学招生名额锐减,他坦然落榜,军营也对他关了门。前进不成,在什么地方栖息一下或游移一下也不能。他有乡村,便只得归去。这种下下结局对父亲是希望的破灭,对陈忠实当然也是希望的破灭,不过这对陈忠实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失败。时在1962年,到处都很困难,他和父亲也无可奈何。
当一个完全的农民,显然不会让陈忠实由衷接受,这是因为他对文学兴趣强烈。在乡村,几乎什么事情都难干,但只要你长着一根对文学产生兴趣的神经,文学却是可以干的。缘于如斯道理,陈忠实变得沉静起来。水深了才能沉静,而且沉静之中也许还潜藏着波澜大惊。
他在乡村当过教师,当过公社干部,这都让他顺利地获得了文章的材料。多年之后,他所听所见的,所经历的,都生动地进入了他的作品。然而乡村给他的不仅仅是这些。
世界上所有经典作品,特别是小说,无不由于地界各异而有独特的文化气息,甚至一国之内也会南有南味,北有北味。风土是会影响作家的,而且会把这种影响渗透在他的文章之中。尼采强调忠于地,周作人研究方域与文学的关系,大约便源于斯。
西蒋村在行政地理上为西安所辖,不过在历史地理上,它归关中,处于白鹿原北坡,灞河之滨。灞河源出秦岭,绕白鹿原而流,曲曲折折,悄然入渭。史书上所谓沛公军灞上,意为刘邦让其部队驻扎于白鹿原,灞上指的就是白鹿原。这里地势崛起,白云任游,可以仗山握水,居高临下,眺望四野而无余。有一天,王昌龄发现斯地很是美妙,便愉悦地隐居了一度。
到陈忠实这一辈,陈家起码有三代生活在西蒋家村。他小时候所玩耍,长大所读书,写作,以至迎妻抚子的庭院,当然是祖居老屋了。有五十年,陈忠实走出家门,在乡村,或到白鹿原和灞河周边的地方去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小麦一黄,便种谷物,谷物一收,便是秋风和冬雪。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而族,族而宗,宗而祖,早就形成了一套秩序,陈忠实开始目染,以后便帮助料理,渐为主持。乡村的这一切,都哺育了他的一种趣味和一种审美。乡村激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阶级斗争,人与人的斗争,也让他获得了一种智慧。
乡村有一个人,也许他对陈忠实的影响比风土对陈忠实的影响更具力量,他便是陈忠实的父亲。父亲的权威在乡村是自然的,不过到十六岁,陈忠实才真正发现了父亲的含义。那年,父亲陪他到学校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地带。小路荒滩,寂然如灭,蓦地草丛一动,父亲说:“狼!”只见一只狼瞪着绿睛,还有一只狼也瞪着绿睛。父亲镇定,从容,不慌不迫,当然影响了他,这使他连一丝一毫的恐惧也没有生出。当然,他对父亲的敬畏特别在于一种道德气场。陈忠实闯荡世界,回家总能感到父亲独具风采的一种目光。陈忠实对这种目光的理解是:不管你做什么,成与败,反正不能把龌龊带到祖居的老屋来。
在中国乡村,父亲显然是一种活的风土,甚至父亲就是大地的印章。陈忠实的父亲大约是一个修身长脸的人,高眉骨,大眼睛,总是岸然而立,神有肃穆,情含豪壮。陈忠实对李遇春说:“我对我的父亲很虔城。”他透露,自己对父亲一直有负疚之感。
不过乡村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面,这个世界还有一面为城市,这也是陈忠实所明白的。他对都市并不拒绝。在工作地址上和户籍登记上,他也早就是城市的一员了。他从自己所在的城市出发到北京或上海去,或到美国去,到罗马去,天下任行,但流淌在他的血液的却一直是乡村所赋于的一种质朴和善良的品质。城市改变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