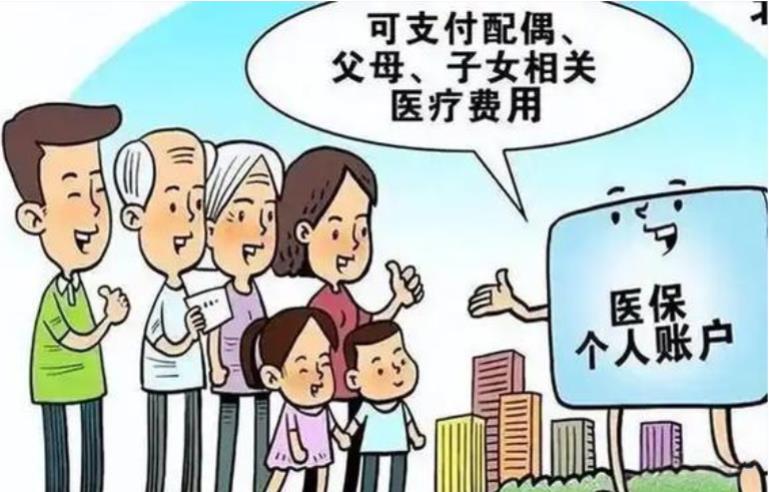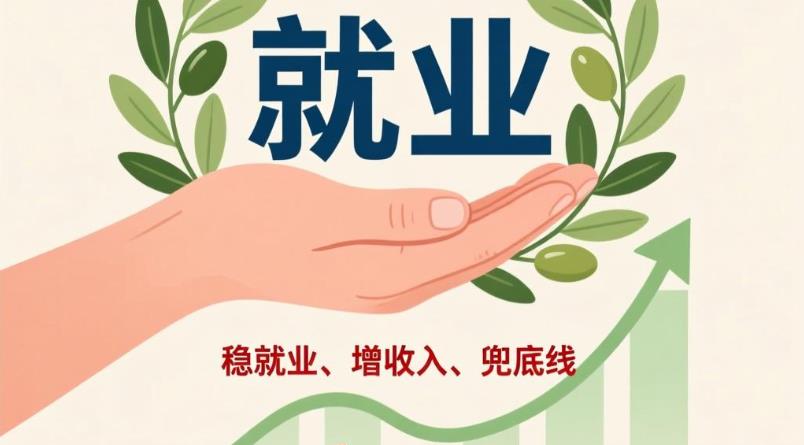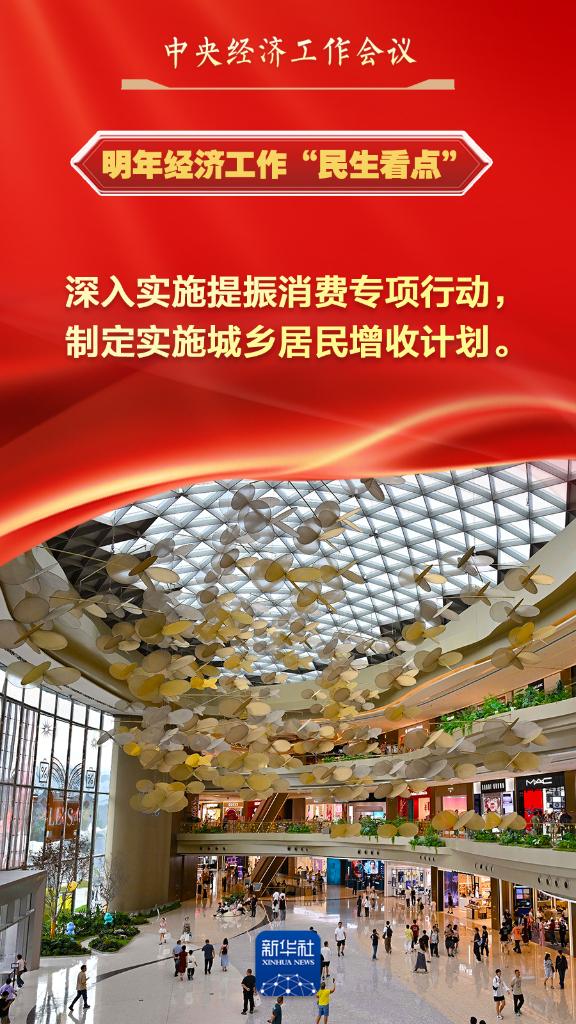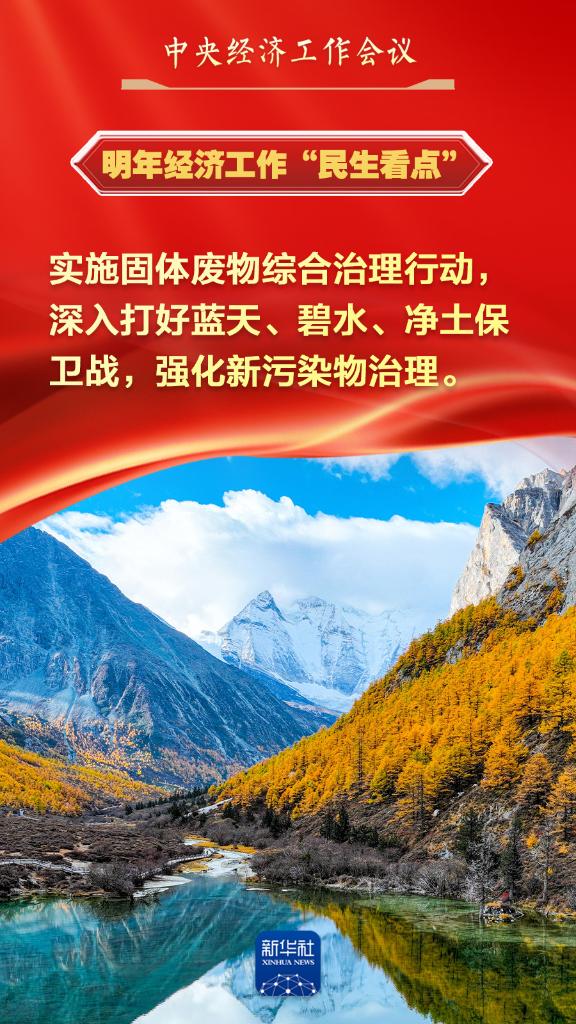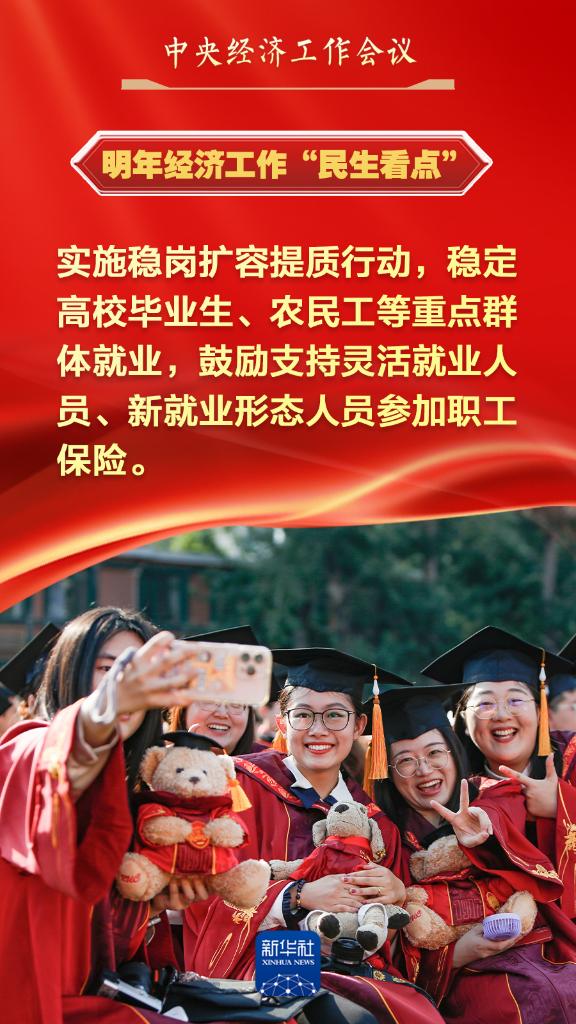在民国的跨国恋中,蒋经国与蒋方良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他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人赋予了“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色彩。
年轻时的蒋经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1925年5月,蒋经国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反帝运动被浦东中学开除,随后他到北京进入吴稚晖为国民党高干子女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以留学苏联为荣。在京学习期间,蒋经国又因加入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队伍被当局关了两周。10月25日,蒋经国终于登上了赴苏的轮船,这一去就是12年,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蒋经国到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成了同学,他思想进步、学习刻苦,一点也没有“官二代”的样子,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赏,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前他成了苏联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按照蒋经国这样的表现,换成别人早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了,可惜他的父亲是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共的“反革命政变”后,远在苏联的蒋经国也受到了牵连,他当即在塔斯社发表《讨蒋声明》,批判蒋介石为“叛徒”,称“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这样的话固然有迫于形势而自保的嫌疑,但对于当时受“左倾”思想左右的蒋经国而言,未必不是肺腑之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的前途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从红军军政学校毕业之后,他要求回国的申请被斯大林驳斥,按照蒋经国后来的话说,自己已经沦为“人质”,随后他申请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也被拒绝。1931年2月,蒋经国被派到“狄拿马”电气工厂当学徒,后又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农村劳动,表现良好的他被选为集体农场的主席。1933年1月他又被调到阿尔泰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10月再调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正是在这里,蒋经国结识了蒋方良。
那时的蒋方良当然不叫蒋方良,而叫芬娜。芬娜那年只有17岁,刚从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厂里工作。芬娜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按照同事玛丽亚的形容,芬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尤其当她绽开笑容的时候,更是清纯而动人。芬娜的个头在俄罗斯女孩中并不算太高,但跟不高的蒋经国在一起,已经是超标准配置了。
蒋经国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这一年他23周岁,正是心理和生理都容易冲动的年龄。之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对方“政治觉悟”太低而分手。这一次他对芬娜一见倾心,利用自己副厂长的身份“以权谋私”,经常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成天嘘寒问暖。果然,情窦初开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芬娜很快就被打动了,和蒋经国确立了恋人关系。
但如果我们将两人的爱情与婚姻“快进”到尾,再回首,的确苏联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浪漫的时光。蒋经国与芬娜在一起无话不谈,一起出去骑单车,一起到海边去游泳,一起在舞会上起舞,这样的雅兴,在蒋经国回国当上“太子爷”后将成为一种奢侈,而在苏联时却成了支撑蒋经国活下去的最大理由。